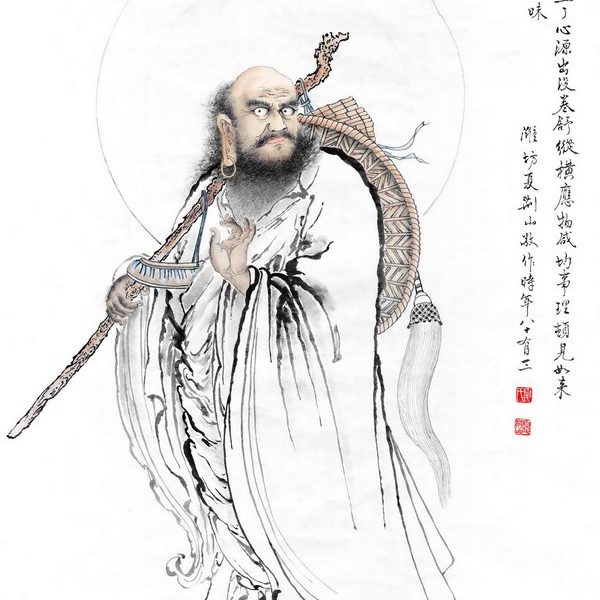禅是「禅那」的简称,梵文:Dhyana,意思是「静虑」,即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,消除妄念,启发真实的智慧。这是禅的学术译义。
从广义来说:修「禅」即是修「心」,所以无论你学习哪一宗派 — 密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、唯识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律宗 — 都是与「禅」息息相关的。一个真实的修行者,无论行、住、坐、卧、语、默、动、静,都离不开「禅」。永嘉大师《证道歌》说:「行亦禅,坐亦禅,语默动静体安然。」所以,禅无处不在,无时不是。
但是,从狭义来说:禅是佛教一宗派,大致可分为「如来禅」与「祖师禅」两种。 「如来禅」(注一)以佛陀所说的经教为圭臬,为文字所诠,故又名「教内禅」;「祖师禅」是不依教内经论,「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」,故又名「教外禅」。
禅宗渊源
根据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记载: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,从南印度来到汉土,弘扬禅法。历代从印度或西域到中原的胡僧,多携有自己所尊奉的经论,为其禅法的依据,唯有菩提达摩未带来一经一论,因为他所传的禅法,「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」。达摩以前的禅师:如安世高、鸠摩罗甚、支娄迦谶、佛陀跋陀罗所弘扬的禅法,都以经教为依据;及至达摩来华后,汉土禅风遂由参考文字的渐证法,变为不立文字的顿悟法。
达摩把禅法传给慧可;慧可又传给僧璨。但由于遭受武帝灭佛的灾难,僧璨没有发展的机会。后来他传给道信;道信传给弘忍。弘忍之后,禅宗分出惠能和神秀南北两派系。惠能一系取得了独尊的地位,而神秀一系则几至式微;因此惠能派系遂发展成为中国禅的主流。
从达摩到惠能,「祖师禅」经历六代。后世称达摩为初祖,惠能为六祖。其实禅宗的宗派形成,直到惠能才大放异彩。他不仅开创了中国禅学,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是禅宗最重要的宝库。
五家七宗
中唐以后,「祖师禅」进入了百家争鸣,万花齐放的时代。六祖惠能的门徒众多,其中以荷泽神会、青原行思、南狱怀让的成就最为显著。相传《六祖坛经》是神会撰述的。他的禅法后世称为「荷泽宗」,但传承甚少;反而当时寂寂无名的怀让与行思两门,渐渐兴盛起来,师承悠远,形成了后来「五家七宗」的禅门派系。
怀让传马祖道一,道一又传百丈怀海。怀海后分出两派:一派由黄檗希运传临济义玄,成为「临济宗」;另一派由沩山灵佑传仰山慧寂,形成「沩仰宗」。
青原行思传石头希迁,希迁下分出两派:一派由药山惟俨传云岩昙晟,昙晟传洞山良价,良价传曹山本寂,建立「曹洞宗」;另一派由天皇道悟四传至雪峰义存。义存下又分出两派:一派为云门文偃,创「云门宗」,另一派由玄沙师备三传至清凉文益,创立「法眼宗」。就这样薪火相传,「五家禅」相继建立,禅宗进入极盛时期。
到了北宋时,「临济宗」经六传到石霜楚圆,又分出两支:一为黄龙慧南的「黄龙派」,一为杨岐方会的「杨岐派」。总括来说,由唐代六祖慧能传承下来,到北宋诸祖,禅宗发展为「五家七宗」。
五家禅宗的「家风」各有不同,但其宗旨则不离六祖的顿悟心性,自我解脱。所谓「家风」就是各宗师接引后学的独特方法,如沩仰宗的「方圆默契,亲切温和」;云门宗的「截断众流,不容拟议」;法眼宗的「对病施药,扫除情解」;曹洞宗的「家风细密,言行相应」;临济宗的「孤危险峻,棒喝并施」。五家中影响最大,延续最久者是「临济宗」。它的「机锋」、「棒喝」、「公案」与、话头」,甚饶禅趣,在禅门流传最广。
机锋棒喝
何谓「机锋」?禅师认为言语文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假借施设,而禅修是心性的体验,必须超越言语文字的规范,才能把「真心」解脱出来,所以他们在教学时,因人因时因地而施行各种不规范的形式去接引学人。
起初一般采用隐语、比喻、暗示、问答等方式;后来进而发展为动作。这些形式大体包括如下几类:
有时,禅师以缄默代表说法。 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四记载药山惟俨上堂而不说法的典故:
「一日院主请师上堂,大众才集,师良久便归方丈,闭门。院主逐后曰:『和尚许某甲上堂,为什么却归方丈?』师曰:『院主,经有经师,论有论师,律有律师,又争怪得老僧?』」
药山禅师认为经律论可以说,但禅是不可说的。所谓:「一落言诠,便成戏论。」言说反而限制了学人的心路意识,得不到「真心」的自在解脱。
有时,禅师以不规范的言语接引学人。 《五灯会元》记载一则赵州从谂与学人的对话:
「学人问:『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?』师曰:『有!』曰:『几时成佛?』师曰:『待虚空落地时。』曰:『虚空几时落地?』师曰:『待柏树子成佛时。』」
这些问答看似同义反覆,自相矛盾。其实,禅师们借助于这种不规范的言语,截断学人的妄心思惟,使令超越逻辑和言语的限制,达到回转反观内心世界的妙用。
《景德传灯录.卷五》记述一则「答非所问」的机锋:
「有僧问:『万法归一,一归何处?』师答:『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,重七斤。』」
问者认为如来藏性住于「某处」,尚在时空的范畴内思惟,未摆脱生灭有为法。师的「答非所问」,暗示学人所修学的与真心风马牛不相及。
禅师有时以动作启发学人。 《碧岩录》第四十二则有庞蕴居士在雪飘中掌打禅师的公案:
「有一天,庞蕴拜辞药山禅师。药山命几位禅徒相送。当大家走到山门时,正值大雪纷霏,众人见此胜景,心旷神怡,欣喜万分。
庞蕴指着空中说:『好雪片片,不落别处!』一禅师立即就问:『落在何处?』 庞居士听后,一掌打在问者的肩膀上,以示启发。」
庞蕴是开了悟的禅者。他说:「好雪片片,不落别处。」,因为这时他心内没有动静二相的妄想分别。好雪片片自上飘下,看似是动态,但其实「万法性空,非动非静,无来无去」。既然雪片重来未动,怎会有落处?禅师不明白庞居士的禅意,生起了计度思量心,所以他问雪片落在何处。他既不懂得领受当前的好风光,反而生起妄念,分别现象的动静、去来相,所以遭庞居士掌掴提示。
……………
何谓「棒喝」?禅师在机锋运用的基础上,为了杜绝学人的虚妄思惟,考验其悟境,或用棒打,或大喝一声,令学人从执着中猛醒过来,当下顿悟自心佛性。相传棒的施用,始于唐代德山宣鉴与黄檗希运;喝的使用,始于临济义玄,故有「德山棒,临济喝之称。」
公案话头
「公案」两个字,本来的意义是唐朝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。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,作为禅者之指示,久而久之成为座右铭。禅门认为这些记录可启发思惟,而且尊严不可侵犯,犹如官府的判决,故亦简称之为「公案」。
这种风气倡始于唐代,到宋代大盛。禅门「公案」大约有一千七百几则,但通用的不过五百几则而已。这些公案都记录在禅宗经典内。
禅宗有参「话头」的法则,但「话头」不就是「公案」。 「话头」是从「公案」中拈提山来的某一句话或一个字,作为参究的对象。以唐朝赵州从谂禅师的「赵州狗子」公案为例,《无门关》第一则云:
赵州和尚因僧问:「狗子还有佛性也无?」
州云:「无!」
无门曰:「参禅须透祖师关,妙悟要穷心路绝……(中略)……如何是
祖师关,只一个无字,乃宗门一关也。」
这「无」字是「话头」,而「赵州狗子」整个言行记录是「公案」。
佛经不是说众生皆有佛性吗?为何赵州禅师说狗子无佛性呢?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?其实禅师借公案之「非逻辑性」来截断学人一般偏执的思路和意识逻辑的推理,从而引发他们的疑情,启迪内心的「实相般若」。
有人来问佛教,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,就成为自己的知见,当下成为法执。如果不用言语文字就无所显示,所以「公案」成为了禅门方便的参究和研讨的工具。
临济宗宗杲禅师提出一种参禅方法,不必默照,亦不必参究「禅门公案」,只要将某公案内某句关键性的「话头」提出来,时时参究,努力不懈,紧参不放,假以时日,就能够开悟,这就是参「话头」。
最常见的话头有: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?」、「狗子有没有佛性?」、「念佛是谁?」、「万法归一,一归何处?」、「庭前柏树子」、「无」等。
参话头并不是文字上的推敲,亦不是理性逻辑上的思量,是要行者起疑情。所谓大疑大悟,不疑不悟。当你不断地去参究,妄念会愈来愈少,到后来只有一句话头存在。当话头的疑情尽消时,就是悟处。
禅宗经典
自唐代《六祖坛经》面世后,禅门遂大开语录之风。所谓语录,是禅师们的言行记录,包括开示与问答,通常是门徒在禅修期间所编汇的。除各家个别的纂集外,还有统贯性的语录:如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续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碧岩录》、《从容录》、《无门关》、《古尊宿语录》、《正法眼藏》、《指月录》、《宗门统要》、《永平颂古》等著作。
「祖师禅」既标榜「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」为宗旨,为何又参究语录呢?其实,禅宗「不立文字」的意思,是不执着文字、经教,并非厌弃文字,或舍离经教。言语是用作表达道理的,它本身并非道理。初学者要依言以会道,至于会道后,就应该合道而忘言,不能执着言语。文字犹如渡河之木筏,及至彼岸,则必须舍筏而登陆。
其实,初祖达摩至四祖道信传授禅法时,亦以《楞伽经》为依据。 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记述:「达摩谓:『吾有《楞伽》四卷,意用付汝,即是如来心地要门,令诸众生开示悟入。』」六祖惠能是听闻《金刚经》而开悟的,所以他力劝禅者受持《金刚经》。禅宗并非不依文字,而是教人不要拘泥于文字。禅者要跳出思惟逻辑的规范,文字的限制,才能证入无限的内心世界啊!
这些经典,是历代禅师智慧的结晶,是学人的「标月指」(注二),其典籍数量庞大,数以万计,文采瑰丽,字字珠玑,是中国哲学、文学、历史的文化宝藏。
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。禅宗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,所以太虚大师说:「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。」他所指的就是「祖师禅」。诚然,禅宗在中国影响深远,是最具特色的佛教宗派。
(注一:请参阅温暖人间116期广结善缘专栏拙作「如来禅」,内容略述如
来禅的意义与修行次第。)
(注二:指示月之指,称为标月指。佛教将「真如」比喻「月」,故对不知
真如(月)者,以种种法来说明(指)真如(月)的实相。)